
时代的灵魂……舞台的奇迹……你的艺术是永恒的纪念碑,只要你的书在,你就永远活着……他不属于一个时代,他属于千秋万代。
——【英】本·琼森
当我读到莎士比亚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
——【德】歌德
关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整个的戏剧情形,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写起戏来,大体如美国作家爱默生所言:“莎士比亚的青年时代正值英国人需要戏剧消遣的时代。客栈庭院,不带屋顶的房子,乡村集市的临时围场,都成了流浪艺人现成的剧院。人们喜欢由这种演出带来的新的快乐……它既是民谣、史诗,又是报纸、政治会议、演讲、木偶剧和图书馆,国王、主教、清教徒,或许都能从中发现对自己的描述。由于各种原因,它成为全国的喜好,可又绝不引人注目,甚至当时并没有哪位大学者在英国史里提到它。然而,它也未因像面包一样便宜和不足道而受忽视。”
包括托马斯·基德、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森在内的一大批与莎士比亚同时代,且名气并不在他之下的诗人、戏剧家,全都突然涌向这一领域,便是它富有生命力的最好明证。
那时的情形是(今天也未必不是),对于为舞台写作的诗人(今天的编剧大多已不是诗人),没有比通过舞台把握住观众的思想更重要的事,他不能浪费时间搞无谓的试验,因为早有一批观众等着看他们想看的,那时的观众和他们期待的东西非常之多。

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当他刚从外省乡下的斯特拉福小镇“漂”到帝都伦敦搞“文创”时,那儿的舞台早已经开始轮流上演大量不同年代、不同作家的剧本手稿。
众口难调,有的观众对《特洛伊传奇》每周只想听一段,有的观众则对《恺撒大将之死》百听不厌,根据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改编的故事总能吸引住观众,还有观众对演绎从传说中的亚瑟王直到亨利王室的大量历史剧十分着迷。总之,连伦敦的学徒,都能对许多凄惨的悲剧、欢快的意大利传奇,以及惊险的西班牙航海记耳熟能详。所有这些历史、传奇,上演之前都或多或少经过剧作家的改编加工,等剧本手稿到了舞台提词人的手里,往往已是又脏又破。
时至今日,早没人说得出谁是这些历史/传奇剧的第一作者。长期以来,它们都属于剧院财产,不仅如此,许多后起之秀又会进行修改或二度编剧,时而插进一段话,植入一首歌,或干脆添加一整场戏,因而对这多人合作的剧本,任何人都无法提出版权要求。好在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不想把版权归个人,毕竟读剧本的人少之又少,观众和听众则不计其数。何况剧作家的收入源于剧院演出的卖座率及股份分红。就这样,无数剧本躺在剧院里无人问津。
莎士比亚及其同行们,十分重视这些丢弃一旁、并可随拿随用的老剧本。如此众多现成的东西,自然有助于精力充沛的年轻戏剧诗人们,在此之上进行大胆的艺术想象。
无疑,莎士比亚的受惠面十分广泛,他善于、精于利用一切已有的素材,从他编写历史剧《亨利六世》即可见一斑,在这上中下三部共计6043诗行的作品中,有1771行出自他之前某位佚名作家之手,2373行是在前人基础上改写,只有1899行属于货真价实的原创。
这一事实不过更证明了莎士比亚并非一个原创性的戏剧诗人,而是一个天才编剧。但不得不承认,且必须表达由衷钦佩的是,莎士比亚是一位世所罕见的顺手擒“借”的奇才,干脆说,他简直是一个既擅、又能、还特别会由“借”而编出“原创剧”的天才。不论什么样的“人物原型”“故事原型”,只要经他的艺术巧手灵妙一“借”,笔补神功,结果几乎无一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原型”销声匿迹无处寻,莎剧人物却神奇一“借”化不朽。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无不如此。因而,对于莎翁读者、观众,尤其学者,不论阅读欣赏,还是专业研究,都仿佛是在莎士比亚浩瀚无垠的戏剧海洋里艺海拾贝,无疑,捡拾的莎海艺贝越多,越更能走进他丰饶、广袤的戏剧世界。

不光莎士比亚,生活在那一时代的戏剧诗人或编剧们,大都如此“创作”,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作品的原创性兴致不高,兴趣不大。换言之,为千百万人独创的文学,那时并不存在。在那个还没有文学修养的时代,无论光从什么地方射出,伟大的诗人都把它吸收进来。他的任务就是把每颗智慧的珍珠,把每一朵感情的鲜花带给人们;因此,他把记忆和创造看得同等重要。他漠不关心原料从何而来,因为无论它来自翻译作品,还是古老传说;来自遥远的旅行,还是灵感,观众们都毫不挑剔,热烈欢迎。早期的英国诗人们,从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乔叟那里受惠良多,而乔叟也从别人那里吸收、借用了大量东西。
莎士比亚是幸运的!
以《哈姆莱特》为例,它既是莎士比亚戏剧生涯“两个世纪”的分水岭,也是里程碑,以他开始写这部不朽之作的1600年来划线,如果他在这一年去世,后人只能随着16世纪的结束看到他上一个世纪的剧作,而所有这些尚不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天才。他在揭开了17世纪新纪元之后的短短几年里,接连为时人,更为世人,奉献出后来者难以逾越的堪称戏剧巅峰之作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
即便我们不能说《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剧作中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一部,但可以明确地说,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创造的最伟大、最永恒的一个戏剧人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他就像莎士比亚一样,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只要人类存在,他的灵魂便永远不朽。莎士比亚在他身上挖掘出了人性深处最丰富、最复杂的隐秘世界,在我看来,莎士比亚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永恒的生命孤独者。显然,这样的塑造又是与他天才的艺术构思和想象密不可分。
“有一千个读者(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照这句话,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千分之一个“哈姆莱特”。这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躲藏在灵魂深处的自己。如法国史学家丹纳所说:“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不仅感受到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还感受到许多我们所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他具有不可思议的观察力,可以在刹那间看到一个人完整的性格、体态、心灵、过去与现在,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与深度以及剧情所需要的准确的姿态与表情。”
爱默生认为,莎士比亚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出类拔萃的才智:“一个好的读者可以钻进柏拉图的头脑,并在他脑子里思考问题,但谁也无法进入莎士比亚的头脑。我们至今仍置身门外。就表达力和创造力而言,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他丰富的想象力无人能及,他具有作家所能达到的最敏锐犀利、最精细入微的洞察力。”
在此,仅举一个小例子:“Tobe,or nottobe:thatisthequestion。”这几乎是莎士比亚为哈姆莱特量身定做的最为人知的一句台词,而且,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的是朱生豪的译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在英文里,显然没有“值得考虑”的意思。梁实秋将此句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并注释说,因哈姆莱特此时意欲自杀,而他相信人在死后或仍有生活,故有此顾虑不决的独白。梁实秋的“这是问题”简单而精准。孙大雨的译文:“是存在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同样精准。照英文字面意思,还可以译出多种表达,比如,“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或者“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活着,还是死掉,这是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1603年印行的第一个四开本的《哈姆莱特》中,此句原文是:“Tobe,ornottobe,Ithere'sthepoint。”按这个原文,译成中文,意思是:“对我来说,活着还是死去,这点是最要命的”。或“我的症结就在于,不知是该活着,还是去死”。或“最要命的是,我不知是该继续苟活于世,还是干脆自行了断”。无论哪种表达,均符合哈姆莱特此时在自杀与复仇之间犹疑不决的矛盾心绪。而“值得考虑”四个字,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哈姆莱特在严肃认真、细致入微地思考着关于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这个哲学问题或命题,而不是自己的生与死。
从“第一四开本”的印行情况来看,“Ithere'sthepoint”作为最早演出时的台词,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但出自演员之口并非没有可能,而“thatisthequestion”显然是修改之后作为定本留存下来的。不过,无论“thepoint”(关键)还是“thequestion”(问题),意思都是“关键问题”。因此,在这个地方,我愿把它译成:“是活着,还是死去,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这自然是个人的一点理解。但我想,若把深藏于莎士比亚不同版本里诸如此类的微妙多多地挖掘出来,会十分有意思,至少非常有趣。
《奥瑟罗》是“四大悲剧”中的一个例外,例外在于它出现了两个男主人公。
英国著名戏剧史家约翰·尼科尔在其皇皇六卷本的《英国戏剧史(1660-1900)》中说:“在一些悲剧,尤其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中,男主人公不仅有一个,还会有两个,而悲剧情绪就来自这两位主人公的个性冲突。《奥瑟罗》的男主人公到底是谁?可以说,奥瑟罗本人在最后一幕之前,没做过任何事。我们在这部剧中看到了两个主人公:伊阿古以一种人性中的可怕弱点,玩弄着一个冷酷无情的欺骗把戏;奥瑟罗则以另一种不同于伊阿古的人性弱点,逐步走向自我毁灭。它不像《哈姆莱特》和《李尔王》那样的戏,只有单一的男主人公。”
不必讳言,以刻画人物性格来说,伊阿古是《奥瑟罗》剧中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在舞台上似乎更是如此,他一张口说话,一举手投足,便浑身充满了戏。奥瑟罗、苔丝狄蒙娜、凯西奥,更别说罗德利歌,都是他手里操控的玩偶。他牵动着他们,同时也牵动着剧情演绎的每一条神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几乎抢了所有人的戏。《奥瑟罗》因伊阿古而悲得出彩、好看。甚至可以说,悲剧《奥瑟罗》的艺术成功,不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叫奥瑟罗的“愚蠢的”被害之人,而多半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叫伊阿古的“精彩的”害人者。假如两个人的戏份儿加在一起是10分,伊阿古至少占6分。比较来看,奥瑟罗更像一个速写白描的粗线条人物,虽有棱角,却处处显得硬邦邦的,而伊阿古简直就是一个三维立体的魔鬼化身,那么逼肖,那么鲜活,那么富有大奸到极点的灵性,那么富有大恶到透顶的魂魄。
没错,伊阿古就是一个彻头彻尾、邪恶阴毒、罪不容诛、该下地狱、永劫不复的卑鄙恶棍、流氓无赖、奸佞小人,把一切形容坏人的毒词恶语一股脑全倒灌在他身上,诸如卑劣、无耻、龌龊、阴险、好色、贪婪、歹毒、奸恶、残忍、冷酷、无情、嗜血、小肚鸡肠、猜忌成性、口蜜腹剑、利令智昏、诡计多端、背信弃义、心狠手辣、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之类,一点也不为过。在莎士比亚笔下,伊阿古堪称坏人堆里的人尖儿,即便放到世界文学专门陈列坏人的画廊里,纵使不能抢得头牌,位列三甲绝无问题。

伊阿古不信天堂,邪恶就是他的人性恶魔,是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是他生命的本钱和人生的指南。如此,莎士比亚创造的伊阿古这个文学艺术形象,具有了一种象征意味,即伊阿古就是那个寄居在人心最黑暗处优哉游哉的魔鬼的代表,一方面,他预示着人类一旦打开心底的潘多拉盒子,把这只魔鬼放出来,它就会不择手段地把人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直至将其毁灭;另一方面,他的邪恶本身又是折射人类龌龊人性的一面镜子,它无情地暴露出,面对笑容可掬到讨人喜欢的魔鬼的诱惑,人类会变得多么愚蠢,多么脆弱,多么容易上当受骗,又是多么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当玩物,以致行为荒诞、人格缺陷、意志薄弱,像奥瑟罗一样,最后走向自我毁灭。
不论从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还是从伊阿古、麦克白,都能断言,莎士比亚看透了我们!无论是他那个时代的“我们”,还是今天的,抑或未来不断延续着的“我们”。不是吗?从人性上看,莎士比亚所挖掘的伊丽莎白时代人性上的龌龊、卑劣、邪恶,并不比“我们”现在更坏,而今天“我们”在人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尊严、悲悯,也不见得比那个时代好多少。
在此,我们要谈及两个非同寻常的话题:
第一,莎剧文本与舞台演出的关系。
尽管莎士比亚最早是为了舞台演出而写戏,(也许仅仅为了多挣钱),尽管莎剧演出史已超过四个世纪,但仔细揣摩查尔斯·兰姆200年前说过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兰姆始终认为,高山景行的莎剧,那一点一滴的原汁原味,都只在他剧作文本的字里行间,舞台上的莎剧无滋无味、无韵无致。换言之,莎士比亚的文本诗剧与舞台演出本是云泥之别,莎剧只能伏案阅读,根本不能上演!
时至今日,该如何理解兰姆呢?一方面,兰姆所说并非无的放矢,他那个时代雄踞舞台之上的莎剧,的确多经篡改,原味尽失;另一方面,兰姆意在强调,由阅读莎剧文本生发出来的那份妙不可言的文学想象,是任何舞台表演所无法给予的。莎剧一经表演,文学想象的艺术翅膀便被具象化的舞台人物形象束缚住,甚至限制死。
第二,莎剧戏文与《圣经》文本的关系。事实上,对于读者或观众的欣赏和理解来说,这一点比第一点更为重要。
英国著名莎学家弗雷德里克·博厄斯说:“《圣经》是莎士比亚取之不尽的源泉,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就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换言之,莎翁作品凝结着《圣经》的“精神结晶”。英国文学教授彼得·米尔沃德牧师甚至断言:“几乎《圣经》每一卷都至少有一个字或一句话被莎士比亚用在他的戏里。”
的确,莎士比亚对《圣经》熟悉到了完全能随心所欲、不露痕迹、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境地。在全部莎剧中,几乎没有哪一部不包含、不涉及、不引用、不引申《圣经》的引文、典故、释义。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尽力去寻觅、挖掘、感悟和体会莎士比亚在创作中是如何把从《圣经》里获得的艺术灵感,微妙、丰富而复杂地折射到剧情和人物身上的。因此,如果不能领略莎剧中无处不在的《圣经》意蕴,对于理解莎翁,无疑是要打折扣的。
从这个角度说,丰富的注释、翔实的导读,不失为解读、诠释莎剧的一把钥匙,也是开启他心灵世界精致、灵动的一扇小窗。
提及莎士比亚,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说:“恐怕这是所有诗人中最伟大的名字,一个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天长地久,莎翁不朽!
研学福利:作家带你去英国提到英国,一定会想起莎士比亚,一个诠释了整个世纪、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

这个夏天8月10日-20日,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家名师——董正锋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开启经典名著夏令营——品读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探寻莎翁生平足迹,场景式深度沉浸体验,领略英国人文历史,感悟十六世纪一代文豪的传奇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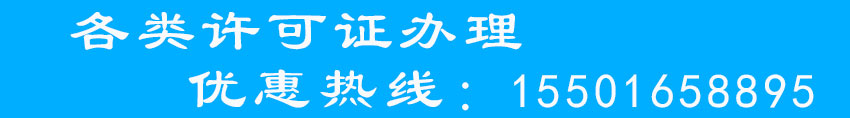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